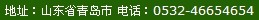|
海伦·福斯特·斯诺 ?一九三二年萧克才二十三岁时,就受命指挥有名的红军第六军,成了中国共产党军队最年轻的高级指挥员。不久,他就名闻中国了。他的部队和贺龙的部队在湘鄂苏区联合起来以后,这两个走在他们的快速突击部队最前面的人,就使历史迅速地前进了。 ?在这支不断运动的军队中,萧克所部无疑是最机动的构成单位了。我访问他时,他不断地在动,在条凳上滑动,在房间里阔步走,猛烈敲打桌子,在愤怒的时候,突然高呼起口号来。不过他负过十三次伤,有某种程度的神经质。他是造举止缓慢的陈腐儒教的反的极好模范。 ?一九三七年,萧克被任命为红军第三十一军军长,帮助这支军队进行改编。抗日战争初期,他在晋绥地区任贺龙统率的第一二O师副师长,但后来他成为“晋冀察解放区”首长聂荣臻的副司令员。 ?我觉得同这位非凡的人交谈是心神爽快的,因为他有着许多精确的事实和数字——这和大多数中国人不同,他们对数学上的细节甚少兴趣。萧克本身就是对中国人旧有的谦卑行为的完全革命。他知道自己的价值,而且了无顾虑地对它进行评价。他的独特之处是,他记了他曾参加的一百七十次战斗的日记,我问他曾负伤多少次时,他在纸片上写下了确切的日子。他做什么事情,总是一干到底,有始有终,决不儒教式地半途而废。像周恩来、徐向前和毛泽东一样,萧克是中国人所称的“军人学者”的再世。 萧克: ?我父亲是一个儒教徒,是个秀才,那是清朝官绅等级中最低的了。一九二一年以前,他过着瓦解中的中国乡绅生活。在那一年里,他破产了。我的家有八、九个人——包括我的两位哥哥,他们的经历同我一样不平顺。大哥被控告同土匪有关系以后,一九二三年四月遭处死。另一位哥哥同我要好,一九二五年参加共产党,后来加入红军,在作战中牺牲。 ?我们的家是在湖南嘉禾县。我一九O七年七月出生。?我六岁时入私塾学习孔子和孟子所有的古书——四书和五经,我是不喜欢这些东西的。五年后,我到高等小学去读了三年。接着,我在初级师范学校度过两年半时间,接受当小学教师的训练——这是破产士大夫的子弟的通常职业。?约十七岁的时候,我就停止就学了,一九二六年我到广州去从军。我加入蒋介石的宪兵团当普通士兵。那时候,我以为他是一个革命领袖,因此他给我留下良好的印象。直到一九二七年的反革命开始以后,我对他的信任才完全垮下来。我曾经把他看作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和左派——我是非常尊重三民主义的。 ?我要到广州去,因为它是革命的中心。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一位在广州大学就读的表兄曾把革命书籍寄给我,包括孙中山写的书。(顺便一提,早几天我接到这位表兄一封信,问我实际上是不是过去常常接到他寄出的书的人。我回信说是。我一看到信封,就认出他的笔迹了。)我马上对这些书籍发生兴趣,特别是对孙中山写的《心理建设》和《伦敦蒙难记》。然而,甚至在这以前,我就已经通过阅读《宋教仁传》而接受影响,倾向革命了,宋教仁是著名的国民党领导人,为反动派所暗杀。另一部影响我的书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传》。我读这部书时,大哭了一场。 ?我家乡的人和亲属是保守的,他们头脑封建。我读了这些书,主动地提高了我的思想。 ?此外,我也对军事科学感兴趣。一九二四年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贪婪地读了《孙武兵法》、《七家兵法》一类中国古代的军事书籍。我还记得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凡尔登战役的记载非常感兴趣。 ?多数人以为我是广州黄埔军校学生。这是搞错了。不过我在宪兵团当兵的四个月期间,我无意地获得了我自己的黄埔军校知识。虽然我很年轻,但我记得我所听到的。吸收黄埔军校军官的全部知识,对我来说是不费力的,因此我像他们一样有知识——靠张开耳朵来听嘛。 ?在广州,我参加了蒋介石的宪兵第六十五辅助团。我起先当军士,看管军火库;后来,军官们注意到我懂得军事,于是使我成为部下,目的在于准备提升我当排长。然而,几个月以后,我就离开宪兵团了,一九二七年,我参加了共产党员叶挺指挥的著名第二十四师。这是张发奎的“铁军”第四军最好的一个师。我任连政治指导员。 ?虽然我只是一个政治指导员,但在北伐期间,我总是和军官们一道在前线指挥士兵。营长认识到我的能力,因此在河南汝南县作战中碰巧连长不在时,就让我指挥这个连。在这次作战中,我起了如此值得注意的作用,因此我暂时代理连长。 ?我们回武汉时,我名义上依然只是政治指导员,但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时,我就凭本身的资格而成为连长了。 造儒教家庭的反 ?直到一九二七年六月,即同国民党分裂以后,我才参加共产党。早在那年二月,一位朋友就同我谈论过,他断言蒋介石正在背叛革命,反对农民和工人运动。这使我生气我疑心起来了。接着在二月末,我回到武汉去了解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在那里,我收到我的共产党员哥哥的一封信,他说蒋介石已经背叛了,并且正在密谋独裁。我心里想,如果是确实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打倒蒋介石,否则革命就会失败。接着,当整个国民党本身变成反动时,我就认识到,只有共产党人才有解决完成革命任务问题的办法,只有士兵、农民和工人?才会坚持下去。南昌起义时,我指挥了我那个连。叶挺指挥的那个师全体士兵参加了起义,因为由上到下都建立了共产党组织。没有一个人开小差。 ?由国民党员转变为共产党员,对我来说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虽然我的家庭是绅士家庭,但正在落魄、破产,直到我父亲只拥有六亩土地。我上学时,对我的家庭来说,交束脩是一个大问题;我穿的是破旧衣服;塾师常常打我,不把我的破产家庭放在眼中。一当我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我就真心赞同,特别是对于联合农工和联共联俄的政策。我对这最后一项政策的信念是如此强烈,以致在资产阶级背叛了它时,我就非常憎恨反革命分子了,并且认为要拯救国家,必须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不能把我看作是知识分子,我只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农民。我五岁至七岁时,是一个胆子小的孩子,在私塾读书时,学习完毕后就劳动,照管农务。我懂得怎样耕地和播种,我一直深切同情农民。起初,我只有一种农民意识。大革命时期在武汉,我看到了实际行动中的中国工人阶级,而在此以前,我对城市无产阶级的情况是一无所知的。我曾经生活在一个封建小镇里,那里只有少数几个木匠和砖匠一类的劳动者。 ?由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对我来说革命有着两种主要的意义:为了达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平等,打倒帝国主义(不仅包括英国,而且包括一切外国强国);打倒封建绅士和地主,包括封建军阀。 ?革命以前四、五年,我已经阅读了关于不平等条约、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等等问题的?书。那时候,我不仅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且是一个领土扩张主义者——我抱着一种狭隘的、妄自尊大的希望,即中国会打倒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并依次征服它们。逐渐地,我的思想改变为只希望中国得到独立和自由。我认为,我倾向革命的主要推动力是反对帝国主义即民族主义。 ?不过我也憎恨地主。我还记得,我十四、五岁时,我父亲打发我去给地主交毂祖。我的家庭是绅士家庭,没法亲自劳动。他们要雇工劳动,并且要从地主那里租地来耕种。那是旱年,因此我父亲吩咐我请求地主减收毂租,由一千四百斤减少至一千二百斤。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磋商。最后,地主只答应减收二十斤毂租,因此我感到很愤怒。然而,当时我只憎恨那一个地主——不是憎恨作为一种制度的地主所有制。 ?当时我也憎恨衙门大官和高利贷者。当我大哥被关进监狱时,家人借了五、六百元来尝试使他获得释放,这笔债成了一种经常的负担。家里从来没有能够偿还。我十四岁时,有一次士兵在我们居住的地区同土匪作战,错把我抓了起来,因此家人要从一个衙门官员那里借来一百块钱,使我获得释放。他们没法偿还这笔钱,因此为了作补偿,我父亲打发我二哥到那个官员家里去教了一年书。 ?我大哥是一个小商人,在土匪中间有朋友和顾客。他被捕好几次,被捕以前,士兵们总是到我家来,威胁说如果家人不付钱给他们,就把他抓起来,并因为他同土匪有关系而将他处死。那五、六百元借款就是在这几次中积累起来的。我大哥最后一次被捕时,因为我们没法借到钱来救他,所以他被处死了。当时我十五岁,他是二十七岁。 这种敲诈勒索以及我大哥被处死,主要是因我自己家庭中的一个地主告密引起的,我恨透了这个地主。只有在我成为共产党员以后,才知道不要搞私人报仇和仇恨,而要从总体上观察腐败的半封建社会问题,并理解我自己的家庭和家庭的衰败只是这种现象的一部份。 我倾向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对中国的旧式家庭制度不满,在这种家庭制度极衰落的狂态中,我体验到这一点。我幼小时,对家庭生活的印象很坏,因此乐意逃避这种生活。自从我离开家庭以来,我从严没有写过信回去。我想我双亲现在都去世了——当时他们已上了年纪,如果现在还活着,会是七十多岁了。我离开时,我母亲认为家里没法筹集再生活五年的资财了。她说,屋子本身这样缺乏修理,它在十年之内必定会倒坍。 连谈到我的封建家庭,我都感到痛苦。但我非常欢喜我的妹妹和我的成为共产党员的二哥?。在一九二八年四月湘南起义以后,我就从来没有再见到这位哥哥了。这次起义以后,他流浪了一段时间,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在湖南常德被捕,但逃脱,参加了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师,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暴露了身份,再一次仅以身免。其后他就在湖北参加了红军。他先是担任军事训练的指导工作,后来任第三独立师参谋长,最后一九三三年年初在战斗中牺牲。 此外,我也有两位姐姐。其中一位的丈夫遭到了一个堕落亲戚的陷害,正像我大哥一样,他因为“同土匪有关系”而被处死。另一位姐姐一九二七年被杀害,他是农会会员。 我强烈嫌恶封建的家庭观念。我父亲很独裁,控制着家庭。家庭处于绝对的独裁之下,我也是这样。在每一点上,我都毫不踌躇地听我父亲的话。他命我不要赌博、吸烟或下象棋,于是我照办。不过,他同时试图以保守的教育来摧毁我的志气。在家里,我不是一个难管束的孩子,但当我暂时免除家庭的羁绊时,我总是无忧无虑而大胆。我还记得我多么喜欢充满喧闹声和自由的农村露天剧场。免除了我父亲严厉的教导及其从孔子和孟子那里引来的呆滞规矩,那是多么宽慰的事情! 我想要离家出走,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在考试前不久,我从一位同情孙中山的老教师那里借了七块钱地主币,在不让我家里知道的情况下离开学校,我穿了七件衣服(这是我拥有的全部衣服了)出发。我离去以前,写了一封信给家里,由一位失学的堂姐妹在我离开后传送。他们收到这封信时,我已经到了广东了。 我一路上踏着积雪走到广东边界上的韶关。人仅有的所有物都放在用我姐姐特别喜爱的外套做的大提包里。我计划出走时,我曾经回到家里去,要拿走我的全部衣物,说学校安排了一次假期旅行,我需要这些衣服。我姐姐定要把最好的外套给我在这次欢乐的旅行中穿! 当时我的念头是要进行历险,并要参加革命,以打倒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我曾经跟我的同学商议此行,但所有四十八个人谁也不赞同我的意图并要和我一起进行。在学校的四位教师中,只有一位没有嘲笑我。这位教师问我历险中有什么成功保证。我回答说我只有着不可征服的抱负,但我晓得这是决不会失败的,他听了表示同情地微笑,就不再说什么了。我始终完全相信自己,相信我的能力和断然的决心。这种信心在十二、三年前就发展起来了,而且自那时候以来,我无所畏惧。一当我相信了一件事情或作出了一项决定,我就毫不动摇地实行了。 (你也知道,尽管我的记忆力极好,但自从这些事件在多年以前发生以来,我从来甚至没有想起它们。) 我现在还记得,在我冒险的第一天中,我走了八十五里路,在一个姓萧的地主家里过夜,他是我祖父的朋友。他家里的人疑心我潜逃,于是留住我,但由于大雪,他们没法给我的家人送消息。五天以后,他们终于容许我随意去,相信了我说的一位表兄在广州给我找到了职业的话。在这五天时间中,地主的两个儿子看守着我,我变得很瘦,因为我非常担扰我的计划可能失败。 我给放出来以后,走了五天的路,到达韶关。到了这时,我借来七块钱已花去了一半。到广州去的火车票是六块钱。我在这个市镇里徘徊,不晓得怎样去凑够这个总数。我在街上碰见一位军官,从他说的方言可以断定他的家乡离我的家乡不远。我向这位陌生人提出我的问题来,于是他给我吃的,替我安排睡的地方,并带了我一同到广州去,在广州,我同过去常常寄书给我的那位表兄见面。这位表兄是广州大学的毕业生。我特别喜爱的那位哥哥也在那里,完成了他在广东军事学校最后一个学期的课程。 我对军事问题比对政治问题更有趣,因此想要进入黄埔军校学习,但一九二六年一期我迟到了两个月时间,所以没法入学 在南昌起义中和叶挺在一起 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义,是国民党对革命的反对的结果,同时是中国革命历史过程的一部分。它符合逻辑地接着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香港罢工和武汉政府而发生,使漫长的革命斗争继续下去。它是对国民党背叛革命的警告。 我指挥的连是叶挺统率的第二十四师的一个构成单位,和第二十四师一道参加南昌起义的军队是:贺龙指挥的两个师,“铁军”的两个团,以及朱德指挥的一个教导团。 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我们到广东省去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次远征广东也失败时,我留在广东,没有钱用,没有朋友。我由广州流浪到韶关和汕头,生活很苦。后来,我短时间地参加了蒋介石的新第十三军。 你问我在南昌和广东失败以后是不是意气沮丧。不,我有着坚强的战斗意志,而且后来我指挥了游击战。在南昌起义中,我那个连只损失了几个人,但在广东一个地方退下却时,却有三十五人牺牲。我们由南昌到广东潮州,行军四十七天,一路上都进行战斗。后来我们到了海陆丰地区,军队就消散了,所以我逃走。在此以后我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只是为了混饭吃,因为穷得可以。我给一个低级军官当秘书,他一点也不知道我的身份。在这次消散中,叶挺离开了红军。我一点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在白军里呆了一个月以后,我回到家乡去。这时我是一个兵,我父亲不敢欺侮我了。我到家后两个星期,高兴地听到朱德的部队已经到了湖南南部的消息。我知道朱德曾经是南昌起义的一位领导人,于是离家(在阳历十二月二十九日,即新年前一天),到我少年时曾留住我五天的那个地主家里去。我想获得关于新红军的消息。我不敢直接问。我假装为把我的行李留在某处而发愁,问这个地主行李会不会“遭到土匪的抢掠”。他强调说会,于是我知道这种传说是确实的了。 我回到家里去,我母亲高兴得哭起来,因为我长期不在,这时却新年好运气,我回到家里来。不过,第二天早上我就带着两位朋友一同离开。我们去寻找起义队伍,三天以后,我们到达宜章县。虽然我没有见到朱德,但却看见农民在村子里继续造反。 朱德领导的湘南起义 在一个村庄里,我同一个有三百名农民的游击组织接触。他们只有三十支步枪,但我教他们警卫、放哨,给予军事训练,这样一来,我就成为这支游击分遣队的指挥者了,我们的队伍规模小,但我们打赢了许多场小仗。我指挥的分遣队在宜章县是有名的。这是在地方党委命令下的游击起义。最高指挥人是胡小海(译者),他在一九三三年牺牲了。 四月,湖南起义失败后,朱德的主力离开这个地区。小规模的游击组织被隔绝。我的游击组织当时只有十六、七支步枪。大多数游击队员是用矛、剑和其它旧式武器武装起来。后来,游击队在桂东附近登上高山,同毛泽东的部队会合。当时,我把我指挥的游击队置于毛泽东领导下,随即前往井冈山,离开宜章县的整个游击组织,有四百人,我指挥的分遣队为数一百人,即使如此,它也是主要的组织了,所有这些游击队都加入了毛泽东的部队。 中国的游击战术是在反对当地敌人的农民起义中产生的,农民又热心又勇敢。虽然他们不懂得什么正规战略,但他们凭经验学会并创造了有效的战术。他们不应用陈腐书籍里的知识。因为他们参加自发的群众斗争,所以他们的战术没有什么特殊的法式。许多论述战术的中国古书含有可以运用于游击战的原则,但不能当作教条来应用。红军的现代游击战术的创立和总结,在井冈山斗争后已由朱德和毛泽东进行了。在此之前,我们没有有机化的体系,自然,像我本人一样,许多人读过古书,并且记得他们。 我对蒋介石的反游击战术所知不多,不过在他的关于“剿匪”战术的书里,他引用了许多曾国藩、孙子和其他古代作家说的话。顺便一提,他在这部书里引用了许多无效的论点。 你要求我说明我的游击战术成功的诀窍。我可没有充分地回答这个问题的准备,不过我随便说答案是:首先,成功是由于游击组织产生于农民起义;因此战士们品质良好,并且不用说比非革命的士兵有纪律性。其次,游击队员非常勇敢而坚决。例如在宜章的一场战斗中,超过一千名“民团”包围了我的游击组织据守的其中一个碉堡;我们只带着三十支步枪,在大清早敌人弄炊的时候,绕到他们的背后进行突袭;他们在一次袭击中就给打败,敌人退却了五里路以后,我们才撤回少量的游击队,没有追击。第三,游击队愿意并且能够秘密而迅速地行动,敌人一无所知——我们迅雷不及掩耳袭击敌人时,他们可能以为我们是在一百里外的地方。第四,游击战士的情报工作出色。我们从群众那里迅速而详细地获得消息,因为他们拥护我拉的革命运动;他们如实地把一切情况告诉我们。第五,白军因为士气不振,所以容易被打败。 起初,“民团”和国民党军队了无经验,把他们打败是简易的事情。后来,他们聪明得多了,因此要消灭他们就比较困难了。正规军喜欢打阵地战,把他们打败还算容易;“民团”运用类似于我们的游击战术,就难以消灭他们了。 正规军士兵比“民团”更乐意加入红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民团”由地主及其子弟控制,因之非常残酷而坚决地进行阶级斗争。他们认为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家庭和财产而同“赤色侵略者”作战。 由井冈山到江西 朱德、毛泽东等专心于井冈山,并在罗霄山脉的湘赣边界上建立了政治组织,这包括了井冈山。因为这个政治组织拥有大量的红军部队和广阔的土地,而且因为这个政治组织首先贯彻执行土地政策,所以它成为共产党地区中最有力、最重要的地区。这旨中国一切革命力量的模范。江西和湖南的敌人好几次试图压平我们,但都给打败了。我们四次进攻永新县,终于胜利地占有它。我参加了所有这些战斗。在井冈山,我任红军第四军一个连的连长。 秋天和冬天期间,朱德带了主力在江西遂川作战,只留下四个连在井冈山防守。我同这个后卫队伍一起。一天到晚我们都在建筑防御工事,或把大米和其它补给口运送到山上去。我自己挑着三十斤大米,每天上山两次。转运粮食是一个大难题;因为山间长着许多竹,所以我们吃竹笋,以便不须运送太多的粮食。那时候,我是我那个团的党代表。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朱德、毛泽东等在井冈山开会,决定留下一一部分人保护后方,朱德、毛泽东他们则出去扩大苏区。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我跟朱德、毛泽东一起离开井冈山,当时我是团长。 我们行军二千五百里,由井冈山来到江西吉安附近的东固,同红军第二团和第四团会合,并休息一星期。随后我们留下第二团,进军福建汀州——通过白沙和广昌。我们捕获并处决了白军的一个旅长,接着占领了汀州。 由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0年秋天,为了创立新的苏区并扩大红军,我们转战江西、福建和广东各地。我们打的大都是游击战。 由一九三0年底到一九三一年,蒋介石对红色地区发动了三次进攻。在这期间,我担任师长,同军队一起作战,不过,在第三次战役中,我有病,虽然我依然同军队在一起,骑着马积极进行指挥。我患了厉害的疟疾,睡不着。 第六军军长 一九三二年九月,我任第六军军长(它是以前在井冈山的原第八军)。就在那时,我离开了毛泽东和朱德,直到两个星期以前在延安这里,我才再次见到毛泽东。实际上,在一九三一年六月二日跟毛泽东和朱德分手以后的一九三六年我们在西康会合,我才再次见到朱德。 一九三三年期间,我们同湖南省军五个师作战一年,也同蒋介石的一些军队作战。我们获得了许多次胜利,打败了国民党的五个师长。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我们由湘赣地区北上,渡过源江和锦江,占领了米山城(编者按:即今江西省高安县。唐曾名米州以有米山之故,亦称米山城),打败了国民党一个师长、一个旅长和另一个师长。接着我们挥兵北指,渡过修水。我们越过湖北边界,进入湖北的通山和通城地区。然后向南回师。三月廿二日,我们到达湖南和江西的旧苏区。蒋介石和何键派了四十六个团来打我们。因为我们只有六个团,所以经过许多场战斗以后,我们不得不退却。 现在我告诉你一椿有趣的事情: 四月,我们跟何键作战,只用三个团就打败了他八个团,俘虏了一个营长、一个师长和一个参谋长。当时,我的弟兄非常疲劳,因长时期行军而瘦下来。有一个团有九挺机关枪,但只有四十发子弹。另一个团有六挺机关枪,但只有九十发子弹。虽然这是一场硬仗,但单是第六军的这三个团就打败了敌人八个团,因为我们革命精神昂扬。我当时是那里的唯一指挥者,但对于获得胜利来说,其他的人当然像我一样重要。 由四月到六月,我们继续作战,进行了三场战斗。这些战斗的胜利比不上上述的一次,但它们依然是重大的胜利。 和贺龙在湘鄂地区 一九三四年八月七日,朱德和毛泽东命令我同贺龙会合,于是我们由湘赣边界出发,渡过湘江,走过广西一部分地区。然后我们又通过湖南西南部,到达贵州东部。在沿河县的一个小村庄里,我见到了贺龙。这是我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以来第一次见到贺龙——虽然南昌起义时他不认识我。我们在贵州和这个村庄里生活在一起,历时一年。 和贺龙及其第二方面军一起,我率领第六军进攻湖南西部的永愿。我们的军队共同打败了敌人十个团,随后占领了大庸、桑植、桃源和慈利,建立了“湘鄂川黔苏区”。我们这个苏区约有一百万人口。我们苏区的其他领导人有任弼时、关向应和王震。 接着,蒋介石和何键派九十个团来攻打我们。我们打了半年仗,终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末打败了蒋介石的进攻。这是红军在一九三五年进行的最重大的战斗,朱德和毛泽东当时在长征途中,比较上是在作战的范围外。然而,我们通过无线电联络,一直同他们保持联系。 那时候,我们打死了国民党第八十五师的师长,还打死了大约十个团长和营长。此外,我们也俘虏了一个国民党师长。他在前天五月十日才获得释放,他想要回到白“国民党”区去。两天以前,请我们吃饭,第二天晚上,我们回请他。(现在,因为抗日统一战线,我们是不计较对国民党报仇雪恨的。) 一九三五年九月,我们在东部逼迫国民党,占领了(湖南)临澧、石门和津市等地,扩大了我们的军队,增加了大约八千名新兵。 第二方面军的长征 接着,我们开始长征。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我们由桑植出发,一连四天,我们不断地战斗,打破湖南省军的两道封锁线前进。我们渡过澧水和源江,在那四天中长驱三百五十里,每走一步都经过战斗。我们占领了新化、浦市等地。这些地方都是富饶肥沃的地区——但可惜我们在路上没有时间没收地主的财产。 接着,我们向贵州省会贵阳进军,在三十里的范围内经过这个地方,占领了贵州西部的毕节等地方。这费了我们三个星期的时间。我们打败了许多敌人的军队,包括两个整师。然后我们退兵,越过四川南部而到达云南东部,像在贵阳一样,在云南省会只三十里的范围内经过。我们是在四川去向徐向前率领的红军第四方面会合的途中。 我们挺进云南西部,占领了许多地区,包括马龙、富民、姚安、楚雄、牟定、祥云、宝川等地,这些地方我即时是没法记得完全了。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我们渡过金沙江(长江上游),在六月二十三日到达西康,胜利地同徐向前率领的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合,同朱德会同。 在那八个月期间,即由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我们离开湖南时到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我们在我们的长征中行军一万里。在那几个月里,在后面追击我们或在前面和侧翼袭击我们的敌人,总共有一百三十个团(一百三十万人)。我军只有二万人。但国民党没法阻挡住我们。我们打败了敌人,到处都把他们甩在后面。 为什么我们得胜呢?这时,萧克敲打桌子,加强语气地大声说:因为中国共产党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因为红军勇敢!因为官兵合作!因为群众支持、拥护我们! 我们只在西康停留两个星期。在七月十四日巴士底日(法国革命纪念日),我们在朱德指挥下向北进军,准备同日本人打仗。我们越过大草地,历时四十画夜。在八月,我们到达甘肃南部。我们在那里逗留了两个星期;接着,我们又向北进军。同关麟徵和胡宗南指挥的蒋介石主力军作战。我们获得大胜。击败了敌人,在十一月二十一日俘虏了胡宗南的一个师长。接着,西安事变在十二月十二日发生,于是内战结束了。 由于共产党的和平政策,我们在西安讲和,因此现在有了一个和平、一致的中国,作为准备抗日战争的第一步。这保证了中国将不会灭亡。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我们有一个优秀的民族。我们不会处于日本的奴役下。我们一定要发扬我们的光荣历史,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文化。所以我高呼:中国自由万岁! 海伦·福斯特·斯诺年生于美国,年8月来到中国,年,海伦.斯诺独自访问延安,采访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并广泛接触了陕甘宁边区的战士、工人、农民、文艺工作者、妇女和学生,她写出了《红色中国内幕》(即《续西行漫记》)一书,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年1月11日,海伦·福斯特·斯诺在睡梦中静静地离开人世,享年90岁. 如果您有兴趣想了解 萧克将军的更多内容 长按白癜风专家白殿疯怎么医治
|
当前位置: 嘉禾县 >萧克是中国人所称的军人学者
时间:2017/12/19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南丰人移动端的便民实体店,百万红包等你抢
- 下一篇文章: 双旗币,光绪元宝,青花瓷碗市场价值表,,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