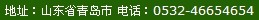|
《尚书·无逸》是反映西周初年思想建设的一篇重要文献。此文诰中周公站在国家兴亡的高度,通过商周先王明君奋勉勤政以兴国保民与殷末纣王奢侈淫逸致身死国灭的正反对比,反复告诫成王要无逸、勤政、爱民,不可沉湎享乐,重逸轻民,以致民怨沸腾,重蹈商纣复辙。此文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对此背景加以分析探讨不仅能加深对《尚书·无逸》的理解,同时也会加深对周公人本思想的认识。 一、天下初定,周公对殷商遗民多措并举,极力安抚公元前年,武王经牧野一战,占领了商王朝京畿之地,迫使商纣王自杀,推翻了殷商中央政权。武王克殷后二年便去世,成王年幼,周公旦摄政代成王行政当国。周公执政后,他深刻地认识到处理殷商遗民问题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并采取了多策并举,软硬兼施的办法。1.对殷商故地施行殷人治殷。周公东征平叛后,为安定殷商故地人民,专门让在殷人中享有很高声望的微子治理殷人。对此,《史记·鲁周公世家》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馀民,以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为使微子能治理好殷人,服从于周王朝的统治,周公“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告诫微子要“往敷乃训,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绥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万邦作式,俾我有周无斁。”微子没有辜负周王朝统治者的信任,继续施行商制,“殷之馀民甚戴爱之”。 2.将部分殷商贵族迁往各诸侯国以分化殷人力量。为了防止殷贵族及追随的方国贵族叛乱再起,行之有效的办法便是将殷贵族及参与叛乱的方国贵族迁至各地,以分散瓦解他们的势力。因而周公将“俘殷献民,迁于九里”,即迁到(成周)洛邑的东郊。同时,周公将一部分殷和方国贵族分封给各个诸侯,由封君把他们带到封国去,以消除他们在原住地区的威胁。如伯禽分得“殷民六族”,康叔分得“殷民七族”,康叔分得“怀姓九宗”。对于分迁的殷和方国贵族,周公采取了威胁和安抚两种手段,反复强调要他们甘心服从周人的统治。这种“宅尔邑,继尔居”,“尚永力畋尔田”的策略确实起到了良好效果,使被迁殷人和方国贵族逐渐稳定下来,极大削弱了殷人的反抗力量。 3.在殷商故地对殷人采取优待政策。卫地处殷墟,是殷商的老窠,也是殷叛乱的策源地,殷人势力尤为强大。因此,卫肩负着镇抚殷人,巩固东方的特殊使命。故而周公将这一重担交付给同母弟康叔,“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故商墟”,即封于商王朝京畿所在地。要求康叔在卫地“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具体做法有三:一是积极向殷先哲遗老学习请教治国方法。如《尚书·康诰》中说:“绍闻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远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训”。这就清楚地指出,要康叔向殷的先王和遗老学习他们统治殷人的方法。二是尊殷旧法,对殷人慎用刑罚。在《康诰》中,周公告诫康叔:“封,敬明乃罚。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可以看出,周公指导康叔采取尊殷旧法,慎用刑罚的政策确实比殷纣一味施行酷刑峻法要高明多了。三是对殷人宽容相待,注重教育。殷鉴不远,商纣王因酗酒淫乐灭亡的惨痛教训,使周王朝统治者不得不警醒。而作为商都的卫地,殷末酗酒遗风更甚,因此周公反复告诫康叔及群臣要“刚制于酒”,而周公也深知殷地遗风在短期内难以消除,因而对殷遗民采取教育为主,刑罚为辅的政策,在戒酒问题上对周人较为严厉,决不姑息。而对殷人则比较宽容,注重教育,“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康叔在卫地认真践行周公的政策方略,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得到了卫地人民的拥护,如《史记·卫康叔世家》所言:“康叔之国,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悦。” 二、周王朝仍面临着诸多棘手问题 作为蕞尔小邦的周族,人数只有六七万,人力物力及文化水平都落后于商王朝,却一战克商,征服了拥有百万人口的广大东部平原,本身绝非易事。輥而周人如何控制殷商广土众民,巩固王朝统治,又更为不易。面对这样的局面,周公等王朝统治者必须处理好几个关键问题: 1.在意识形态方面确立统治身份的正统性。周人非常尊夏,经常以夏人之后自居。如《尚书·康诰》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周人在这里自称“区夏”,亦称自己为“小夏”。从《诗经·大雅·文王》也可见端倪:“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虽旧邦”当指周是夏人之遗,再以受命,以代殷商。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一再宣扬与夏王朝的关系,无非是紧抓人们追念夏王朝政绩的心理,反复强调自己是夏的后代,从而表明周人取代商王朝政权具有身份上的正统性,以在广大民众意识中占有主导权,借以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地位。 2.从天命观方面强调政权获取的合法性。从《尚书·周书》中可以看到,周人反复强调政权的获得是天命转移的结果,由周代商具有合法性。如《尚书·多士》云:“肆尔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乱,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再如《尚书·康诰》云:“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由上可以看出周公、召公等针对殷商遗众笃信天命的特点,强调周人取代商人获得政权,是“天命靡常,惟德是亲”的结果,是应天顺人的,从而表明周王朝政权的合法性。 3.在感情上以殷商圣贤为榜样来增强认同性。周公紧紧把握住殷人怀念和崇尚殷先哲王及贤人的心理,积极宣传自己如何效法殷先哲王,如何尊重殷商贤士,以增强与殷人在感情上的认同性。如在《尚书·无逸》中周公对殷王三宗极力标榜,并与周太王、王季、文王相提并论,大加赞颂殷先哲王的“德”行,以表明商、周圣王先君在“明德、敬德”上的一致性。同时,周人对在商王朝有威望的名臣贤者敬重有加。如灭商后,武王“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又如《吕氏春秋·诚廉》云:“武王即位,观周德,则王使叔旦访胶鬲于次四内,而与之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周人通过对殷先哲王及贤者的推崇敬重,极大地拉近了周人与殷人之间的感情距离,加强了认同感,缓解不同族群之间的心理冲突。 4.营建东都成周,确立政治、军事中心,树立统治权威性。武王克商后,“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从而产生了深深的忧虑,甚至“具明不寝”,通霄达旦不能入睡,其原因是感到“未定天保”。因为武王认识到,牧野之战其结果只是诛纣而已,还未能平其国,殷商的根基尚未摧毁。而作为都城的镐京在黄河以西,对东方的统治,尤其对殷人的控制更是鞭长莫及,因此很有必要在天下的中心洛邑一带建立东都,以有效治理中原,统治天下,“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武王去世后,又发生“三监”、武庚叛乱。周公东征平叛后,为了完成武王遗愿,同时也为加强对东部地区的控制,便历时两年建成了东都成周。在具体措施上,一个是使东西两都的京畿连成一体,形成周王朝统治中心。《逸周书·作雒》云:“制郊甸方六百里,国西土为方千里。”这样,东西两都紧密连接,极有利于西周王朝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另外一个是将大批殷商贵族迁移至成周东郊,以便加强对他们的监督、管理和利用。同时,对殷贵族采用怀柔、利用的手段加以安抚。此后,不但未再见殷人有集体反叛的事件发生,而且使之成为建设东都成周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长期战乱后,体恤民情,
|
当前位置: 嘉禾县 >周公嘉禾文化尚书middot无逸
时间:2021/5/27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周公嘉禾文化ldquo嘉禾rdqu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